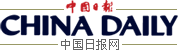《水浒传》二十三回伊始,施耐庵以一段文字简要交待了三位清河县人士:武大、武松和潘金莲之间的关系。他大概不曾料到,几百年后,自己笔下的这三名角色都会有人“相认”。英雄武松也就罢了,关于他的传说早在宋元之际,便已流传于民间。可丑陋懦弱的武大郎,红杏出墙的潘金莲竟也有人前来“认领”?
耳熟能详的故事,往往都有另外一个版本。
世人皆知武大郎矮丑无能,其妻潘金莲貌美放荡,弟弟武松是一代英雄,三人俱为小说里杜撰的人物。可当文学与现实碰撞,又有几人知晓另外一些不那么为人熟知的故事呢?
被冤枉的现实中武大郎
“看官听说:原来武大与武松是一母所生两个。武松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这武大郎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起他一个诨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娘家姓潘,小名唤做金莲;年方二十馀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这使女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却倒陪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
《水浒传》二十三回伊始,施耐庵以一段文字简要交待了三位清河县人士:武大、武松和潘金莲之间的关系。他大概不曾料到,几百年后,自己笔下的这三名角色都会有人“相认”。英雄武松也就罢了,关于他的传说早在宋元之际,便已流传于民间。可丑陋懦弱的武大郎,红杏出墙的潘金莲竟也有人前来“认领”?施耐庵更加想不到的是,他随笔一个“清河县人士”武大武二潘金莲,会令今河北清河县武家与潘家两户人家数百年来生活深受影响,至少,这两家人两百年来,都未曾通过婚。
河北省清河县,据传,正是《水浒传》里的那个“清河县”。这里流传着种种与水浒人物武松武大潘金莲有关的传说。武松的英武,无人非议。与小说描述迥异的是武大郎和潘金莲的形象。人们普遍相信,现实中武大郎确有其人,乃是明朝时清河县孔宋庄身材高大的县令武植,其妻潘金莲,清河县黄金庄人,实为贤妻良母、大家闺秀。
在清河县,“武大郎”武植的坟墓至今仍完整地保存着。其《墓志铭》中道:“武公讳植字田岭,童时谓大郎,暮年尊曰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
不知从哪一代起,清河县孔宋庄武氏后人认定,自家老祖宗武植就是施耐庵笔下的武大郎,许是因为《水浒传》中说武大郎是清河县人,又或是因为“童时谓大郎”的武植,妻子恰好姓潘——武家世代相传、流传至今的家谱中,清晰而简单地记载着:武四老武植,妻潘氏。无论如何,武植的后人以武大郎之后自居,祖祖辈辈守在武植坟前,一代代告诉自己的子孙:《水浒传》里的武大,正是自家被冤枉的祖先。
说冤枉也确实冤枉。如果武植与其妻潘氏确然是武大郎和潘金莲的原型,那倒真可说是艺术源于生活,“低”于生活了。根据1996年重修武植墓时发现的小腿骨测算,武植身高超过1米8,绝非什么“三寸丁谷树皮”;他也不是走街串巷卖炊饼的,武植为人吃苦耐劳,聪明好学,高中进士后,在山东聊城阳谷县做了勤勉奉公的七品县令;其夫人潘氏娴淑贤良,更非出墙红杏;这对夫妻亦绝无可能是武松的兄嫂,因为传说中同出清河县的“弟弟”武松是宋朝人,武大郎武植及妻子潘氏却是明朝人,比武松年轻了两百七十岁有余。
《水浒传》影响清河县武潘两家
既如此,武植夫妇又缘何以那般不堪面目出现在施耐庵的笔下,成了武松的兄嫂呢?对此,清河县人亦有解释。
说起来,这都怪武植一位八拜之交的盟兄弟。这人家道中落,又遭大火,于是去阳谷找做官的武植资助。适逢播种时间,武植政务繁忙,这位盟兄弟在武家住了半月,仅见了武植一面,遂认定武植不够兄弟,故意避而不见,愤然离去。从山东回清河,他走了一路传单是发了一路,说武大丑陋,潘氏淫荡。当他回到家里,却见眼前矗立着盖好的新房,方知武植早已派人为他建房,只是未及相告。武植这位兄弟后悔不已,再回阳谷一路辟谣,却为时已晚。卖着炊饼的丑陋武大与他水性杨花的妻子潘金莲已远传千里,终被同时代的施耐庵写入小说,老孺咸知。
被盟兄弟误会诋毁的武大郎武植,就这样成了武松的兄弟,在故事里死于非命。而当《水浒》传世,清河县仅隔一河的武潘两家便不再通婚。武松杀嫂、大闹狮子楼、斗杀西门庆等故事也为两家人所忌。
传说,抗战期间,冀南边区抗日政府为防水灾,曾派河工委员来清河县动员民工修筑护卫运河堤坝,近百名武氏后人参与其中。堤坝修至油坊镇附近,一个说书卖唱的路过,被河工委员邀请为民工们演唱助兴。这说唱的没唱上几句,就被武家人冲上前去痛打一顿,原来他唱的内容是什么“风流冤孽记”,说的正是武大郎和潘金莲的故事,被武家人认为有辱先祖。听了武家人的解释,河工委们认为武家人为祖先打抱不平可以理解,只是动手打人不对,遂裁定由武家拿出两斗小米给说唱人养伤糊口,了结了这一“蹊跷官司”。
另有传闻,1987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播出了戏曲节目《孙二娘开店》,当电视上出现武大郎,清河县武潘两户人家都赶忙关了电视,跑到院子里放鞭炮,说是“驱瘟神,消丧气”。
《水浒传》里的故事,对清河县武潘两家造成了这样深久的影响。为此,施耐庵直系后人施胜辰曾专程赶赴清河,代祖先向两家后人致歉,武植祠堂里至今仍裱糊着他的诗作:“杜撰水浒施耐庵,潘武无端蒙沉冤。施家文章施家画,贬褒迄今数百年。武植祠里断公案,施家欠债施家还。”
“无端蒙沉冤”不只武大郎
在今日的《清河县志》里,人们可以找到武大郎与潘金莲的传说。但据县志主编沈世远称,自明朝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清河县志》首次修志以来,先后经历了7次重修,其中都没有关于武潘的任何记载。只是因为当地民间传说甚多,在新编《清河县志》时,才以民间文学的形式收录了武大与潘金莲的故事。
至于武大郎武植是否曾出任阳谷知县,沈世远说他曾先后两次前往阳谷县求证。翻看《阳谷县志》时,发现县志内记载的从宋朝到明朝的官吏,均无姓“武”之人。当然,县志所记官吏欠缺很多,没有记载并不等同于不存在。
传说不是历史。施耐庵的武大郎究竟是不是历史上的武植,我们已经不得而知。而把民间故事与历史相搅拌,是地方史志研究里颇为常见的做法,从修史的角度来讲,其实并不可取。虽说如此,当传说影响了几百年来众多真实人物的真实生活,那么,真也好,假也罢,传说本身便也成为历史的部分。
对于清河县武大郎的传说,有学者认为,作为艺术形象的武大武松潘金莲,与其所对应的清河县历史上的三个真实人物,是并存的。小说与民间传说的差异,恰恰证明了艺术真实与真实生活不相等同,艺术真实源于生活基础。
其实,究竟是艺术源于生活,现实塑造了虚拟,还是虚拟的艺术被现实化,艺术的魅力影响了生活,我们实难分辨。
清初王世祯的《香祖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阳谷西门有冢,俗称西门冢。有大族潘、吴二氏,自言是西门嫡氏吴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会,登台演剧,吴之族使演《水浒记》,潘之族谓辱其姑,聚众大哄,互控于县令。”
可见,在《水浒传》的影响下,前来“认领”其中人物的并不只是河北清河县武潘两家人,由此引发的纠纷也可谓历史悠久了。
而正如开头所说,耳熟能详的故事,往往都有另外一个版本,尤其是当艺术遭遇历史之后。不是早有人引经据典地证明过么?“薄幸人”陈世美其实是因不徇私情而遭同学诬陷的清官陈年谷,“杨家将”里卖国求荣的潘美,实为宋朝开国名将,一生为大宋立下了汗马功劳。类似例子不胜枚举,“无端蒙沉冤”的,可并不只有武大郎。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颜台雪) 编辑: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