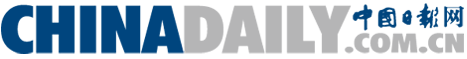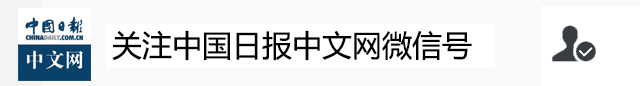消费者们可以模仿出波希米亚的穿衣风格,但学到波西米亚自由自在的精神本质绝不容易。
《加州芒廷维尤的Grateful Dead乐迷》,Roger Ressmeyer摄于1987年(科比斯图片社)
英国著名艺术家大卫·霍克尼( David Hockney )在接受Radio
4电台采访时,宣称波希米亚主义已经消亡。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诗人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也在《波西米亚没有明天》(Bohemia is always yesterday)一歌中,表达了同样的叹惋。
尽管现在这一概念已经渐渐淡出,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波西米亚的形象人尽皆知,它与非利士人资产阶级有着一段爱恨情仇。
波西米亚主义者对世俗的中产阶级爱憎分明,他们是反抗世俗的艺术家,每一件作品都不对中产阶级“胃口”。因此,这些“自暴自弃”的浪子们时常是一贫如洗。但他们视此为反叛的戏装,炫耀他们的衣衫褴褛。他们的横空出世,就是为了对抗这个社会。反叛,就是血脉中的动力因子。
有一些“前斯巴达人”生活简朴,为探索新的艺术形式奉献终生。还有一些则把自己变得性格粗鄙暴躁,用非常规的人生践行自己的艺术实践。在颓废中乐此不疲的“波希米亚人”,不久后惊恐地发现,他们不同寻常的生活极其成功。以至于工业资产阶级们都纷纷效仿,并把它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要知道,这些人可是被波希米亚人所不屑的。到了19世纪90年代,原本远离世俗的巴黎波西米亚区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许多住在蒙马特的艺术家们都被迫逃离这块欣欣向荣的“异教徒仿制之地”。

《巴黎蒙马特大街》 毕沙罗绘于1897年
(卡斯比图片社)
随着时间和商业化的不断入侵,纯粹的波西米亚主义不断被削弱。从乔治·杜·莫里耶( George du
Maurier)的畅销小说《软帽子》(Trilby)到普契尼(Puccini)的经典歌剧《波希米亚人》( La
Bohème ),贪婪的消费资本主义吞噬了这新思潮并把它贩卖给每个人。即使波希米亚主义者们竭力与这些人划清界线。
因此,早期的波西米亚主义是与怀旧主义相捆绑的。真正的波西米亚主义流连过去,纵使都市消费者们可以模仿出波西米亚的风格,但领会它的精神本质绝不容易。总的来说,波西米亚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精神状态。一个“波西米亚人”是在政治上和艺术上拒绝常理,探索禁区并且反转整个世界。
现在,有许多人都模仿波西米亚风的穿着打扮。与此同时,像自由恋爱、同性爱、私生子、大麻和酗酒等早期波西米亚人热衷的事,也被现在的主流人群效仿(除了后两个)。另外,对艺术的观点也由此发生了改变。传统的中产阶级并不像我们想象地守旧,他们喜欢像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那样新潮的室内设计。莫里斯是英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家,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批判十分激烈。他一反维多利亚传统的先锋作品常被人们投以怀疑和敌视的目光。维多利亚现代派的勋贝格和迪亚吉列夫在舞台上常被人们喝倒彩,印象派画家的画作也被批评为乱涂乱抹。
到了现代,我们生活在高度审美的时代,很少有任何一个艺术门类可以引起社会的轰动。新的艺术家和作家轻而易举地就能得到大众的认可,任何形式都能在审美多样化中畅行无阻。
一方面,政策改革的破灭,使波西米亚成为艺术和政治的保护伞。女权主义者、性解放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它的荫庇之下,相互交织出新的文化。在那之前,艺术和政治存在相当的分离性。那时候,政治先锋多是反对艺术的宗教创始人或极端国家主义者。

1966年纽约嬉皮士反越战游行(科比斯图片社)
波西米亚人张扬的个性特征,让同时代的名流避之不及。在上世纪60年代,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通过披头士乐队渗透到青年文化之中。经由摇滚乐的传播成为青年人的嬉皮士运动,这时的波西米亚文化发展出同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它发展成浪荡不羁的明星文化,一日即昌,一夜而逝。此时的波西米亚主义是自我欲望的满足,正如今天的社会名流。
波西米亚文化略显狭隘的目光,有时能够发掘杰出的人才。但明星的挑选是来者不拒的,它虚幻、谄媚和琐碎。这是社会焦躁的一部分,旨在粉碎个人意志的光芒,将个体碾碎成无数毫无价值的碎片。
狂热的消费文化挟持了波西米亚文化,企图整合它每一个新理念。然而,波西米亚的创造力生生不息,但老一套再也不适用当下的传播。
今天,波西米亚文化仍在,但是霍克尼得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寻找它。波西米亚在现代,已然向革命性回归。它根植地下,营养着理论果实,静待盛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