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手机提示的骚扰电话,我一般也是默默掐掉,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只按下静音,让它自己响到放弃。记得张爱玲写过,隔壁家电话铃响又没人接,“一遍又一遍,不知怎么老是没人接。就像有千言万语要说说不出,焦急、恳求、迫切的戏剧”。所以不想接的电话,骚扰度很大,静音而不接,算是一种小小的反击。
碰到面对面的陌生人骚扰,就比较麻烦。曾有朋友情人节前夕被卖花的小女孩追缠,反身吓唬道:“再跟就把你拐走!”似乎有效,但这样自己的形象也就很难看。十字路口,坐在车里无论怎么摆手,总有传单不管不顾地插在后门把手上,或嵌进后视镜面,费你过后一番清理工夫。
我也曾经很羡慕西方人路上向陌生人微笑招手的亲和,反思过自己为什么就做不到。后来有了小孩,发现带着小孩进电梯,走路,就很随意借着孩子的由头:“叫爷爷奶奶,叫阿姨叔叔……”至少出电梯时教他说声“再见”。
然而如果在都市里的电梯,有人藉着这亲和劲儿递过一个手机:先生扫个码支持下创业吧。那时该怎么办呢?当着小孩多半使不出冰默大法,估计会从了。
上周参加一个主题是“公民教育”的沙龙,我的同事施爱东演讲的题目是《乡村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公民教育》,他举了一个关于“大声喧哗”的例子:
在农村,假设我们两个人,老在嘀嘀咕咕地说话,别人可能就会怀疑我们在搞阴谋诡计,别人会说,你干嘛不大声一点说话?你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嘛,你这鬼鬼崇崇的算什么事?有什么话就大声说嘛。所以说,大声说话才是具有正当性的行为方式。我们形容一个人堂堂正正,常常会说他“声音宏亮”。声音宏亮是个褒义词,细声细气,嘀嘀咕咕才是贬义词,鬼鬼崇崇,那肯定是在说东家长西家短,这种说话方式在乡村社会里反而是被人看不上的。
“大声喧哗”这个例子非常普遍。主要由城市居民组成的中国游客团到西方国家,仍然经常因“大声喧哗”而被指责为“没素质”。对此爱东的结论是“谁掌握了主流话语,就会把他自己认为正确的行为方式当成文明的标准,用来衡量另外一种文明形态”,放在中西方的礼仪交流背景下,这样说有道理。入乡随俗,古有明训。然而,在中国社会内部,这样一个各种话语与观念并置的场域,应该怎么处理这种矛盾?
那天我的发言主题是“尊重”。我说以前我想到公民教育的基础,可能会认为是“用正确的知识去教育别人,用正确的观念去引导别人”,现在再想这个问题,会觉得一切交流的前提应该是“对别人的尊重”。
以个人之间而言,总有一个侵扰方,有一个承受方。施与方首先要尊重承受方的规则与感受。比如噪音扰民这事,被扰的人有要求侵扰方降低侵扰的权利。当然要求不能过分,像自己儿媳妇怀孕就不让全楼的人用WIFI这种奇葩要求,就需要第三方加以裁定。
而移到商业场合,这条规则应该更加严厉。为什么会有“顾客是上帝”这句话?因为你的目标是对方的购买或支持,而不情不愿的购买与支持,是效用极低的交易行为。如果商业行为中的承受方认定是骚扰,而侵扰方还不及时收手,还要死缠烂打,或者使用道德绑架的策略,那么整个商业环境就是很糟糕的环境,甚至是一个让人不愿意在其中生活的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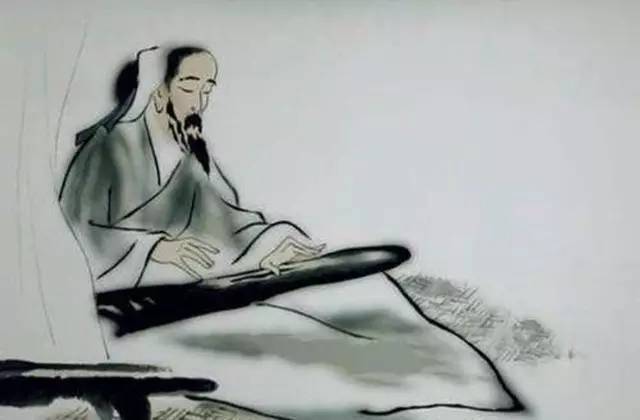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私人空间实在是不够尊重。比如认为小声说话是阴谋,白天关着门就是见不得人,等等。还有在两性关系上,有一句古话“烈女怕缠郎”,所以每年我们都能看到那么多的强行表白,狗血虐恋。我觉得恋爱中的死缠烂打,与生活中的肆意骚扰,二者实在有共通之处,都有一种“ 我要你与你何干”的浑不吝劲儿。
可是在这种痴缠与骚扰中,侵扰方的尊严固是荡然无存,承受方的各种躲避逃离,或忍无可忍的反击,照样是难看无比,整个社会的精神水准,就在这种恶斗中不断下沉。
我觉得最糟糕的一点是,这些陌生人骚扰,往往并非单纯的骚扰,而是带着各种各样的正当性说辞。 最浅层的是“你怎么能这么没礼貌”,高大上一点儿如“献出一点爱心”,终极杀招则是“大家都在XX你为什么不XX”。
天晓得,我的道德情操与家国情怀为什么要向所有陌生人报备与负责?我只是单纯要保护自己的私人空间,同时保护自己的个人尊严。我不相信一个不保护个人尊严的社会,会保护整个社会的尊严。
文?杨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