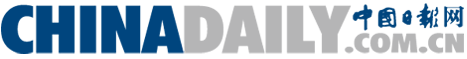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是爵士界最平易近人的人物之一:专辑《泛蓝调调》(Kind of Blue)在一堆无关爵士的专辑中卓荦超伦(图源:马文·科内尔/科比斯图库)
再无其他音乐类型如同爵士乐,能将观众分成如此迥乎不同的群体,为什么?为迎接全球爵士日,BBC文化栏目采访了一位爵士粉丝和一位不喜欢爵士的人,以探究人们对爵士乐的爱恨根源。
缘何心系爵士乐
麦克·霍巴特(Mike Hobart)是《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的爵士乐评论家。
第一次带给我很大冲击的音乐是摇滚。像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他们那一类歌曲。但是这类音乐带来的冲击力渐渐变得稀薄,能量也慢慢衰竭。后来,一个朋友给我放了《雷·查尔斯在纽波特》(Ray Charles at Newport)。我听了这张美国爵士音乐节演唱会的录音唱片后,又感受到了久违的冲击力。
当时是上世纪60年代初,我还只是个伦敦北部长大的青少年。我聆听雷·查尔斯(Ray Charles)和玛姬·亨德里克斯(Margie Hendricks)在《夜晚恰好时分》(Night Time is the Right Time)哼唱祝酒词,倾听萨克斯风手“呆头”纽曼(‘Fathead’ Newman)播撒蓝调,我知道爵士乐就是我想要的。我“融入”了爵士乐:爵士乐赋予我生命和灵魂的感觉,注入我的脑子和身体里。
我对第一次参加的爵士乐现场演奏会依然记忆犹新,那是乐队领队汉弗莱·利特尔顿(Humphrey Lyttelton)在伦敦大牌俱乐部(the Marquee Club)的演奏会。演奏会的整个气氛令我如痴如醉。有人曾告诉我,音乐要么录于曲谱,要么铭记于心。然而在演奏会上,音乐家是音乐的主宰者,参与演奏过程,弥补了音乐自身的缺憾。随后,我意识到,这就是即兴演奏:最杰出的爵士美感芸萃一堂,在演奏的过程中营造自己的秩序。
这就是音乐的另一个伟大之处。音乐至今依然不懈追问秩序、混乱、排列和偶然的问题。然而即便爵士音乐家的即兴创作已成人们闲谈的基础内容,他们的即兴创作方式对很多人来说依然是一个迷。没人和朋友坐在酒吧里喝酒时,会只看曲谱。
为何爵士乐如此振奋人心?因为最好的音乐肆无忌惮,丰富多彩又不断创新。我无法想象再也无法聆听迈尔斯·戴维斯的全景挽歌《西班牙素描》(Sketches of Spain),或是不能体验《查尔斯·明格斯演奏查尔斯·明格斯》(Mingus Presents Mingus)中低音贝司和萨克斯管的激昂混响。两张唱片皆录制于1960年。我知道,未来十年内,我依然会乐此不倦地凝听萨克斯手卡米西·华盛顿(Kamasi Washington)五月五日即将发布的三碟专辑《史诗》(The Epic),在他如火热情和动感活力中沉醉。他的感谢列表里包括了爵士钢琴家迈科伊·泰纳(McCoy Tyner)和嘻哈音乐家莫斯·德夫(Mos Def),但一个月前我连听都没有听过卡米西·华盛顿这个名字。
每每人们认为爵士乐只存在于收音机中,我总是惊讶万分。但是看看主流节目中的伴奏音乐家,往往爵士乐曲名一如既往,出其不意地冒出来。没错,他们像大家一样讨生活。但这就是他们的不同之处。他们从事别人都远离的事业,充实他们的爵士乐想法,同时他们的想法也丰富了流行乐(pop)、嘻哈乐(hip-hop)和节奏蓝调(R&B)。
温顿·马萨利斯(Wynton Marsalis)是一名杰出的教育学家、经营者、艺术指导和演员(图源:莱布雷希特音乐和艺术照图书库Lebrecht Music and Arts Photo Library /阿拉米图库Alamy)
爵士乐的大部分生命历程中,并没有任何正式的爵士乐教育结构。然而如今,爵士已是公认的第一种美国本土真实艺术形态。我曾听鼓手阿特·布莱基(Art Blakey)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对听众这样说过,而正值年青的温顿·马萨利斯恰好是当晚布莱基的号手。马萨利斯如今是纽约唯一一队职业管弦乐队,林肯爵士中心管弦乐队(Jazz at Lincoln Center Orchestra)的艺术指导。
马萨利斯依然是回顾昔日的节点,坚持不懈作曲,巡回演出,与其他类型音乐家合作。他献身教育,贡献非凡。通过他这一类人的不懈努力,如今爵士乐学习在全球成为正式教育,每年都会有成百上千技艺精湛的爵士乐家学成毕业。一些人认为这是消极的,会导致精于技艺却狭隘封闭的音乐形态。重申一遍,如同其他任何领域,一旦你关注其中佼佼者,(何乐而不为呢?)你会发现,爵士乐从跨文化融合物演变成前卫先锋,无时无刻都在爆发着活力和创意。
缘何痛恶爵士乐
贾斯汀·摩耶(Justin Moyer)是《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专栏作家。
我曾经喜欢过约翰·科川(John Coltrane),后来我对他深恶痛绝。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身边没有人听爵士乐。爵士乐就像恐龙一样,早早就灭绝了。爵士乐只是一种模糊的音乐种类,当摇滚吉他手煞有介事地表示渴望像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或奥内特·克莱曼(Ornette Coleman)等萨克斯风手一样演奏时,《滚石杂志》才会提及它。爵士早已没落多时,当然,没人买爵士乐专辑:最畅销的爵士乐唱片,迈尔斯·戴维斯的《泛蓝调调》美国销量不过四百万张,然而摇滚乐手艾拉妮丝·莫莉塞特( Alanis Morissette)的专辑《参差小药丸》(Jagged Little Pill)销量超过了一千五百万张。
对于一个长在费城郊区的青少年来说,口袋里没有多少零花钱,也没有车,没有网络的帮助,要理解科川是很艰难的。科川逝于1967年,比我的出生早了整整十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了一家唱片店,在唱片架上随手挑了他的一盘磁带,仔细辨认再版唱片盒上几乎消失无踪的说明文字,重复地听着他的歌玩任天堂,久而久之养成了欣赏《大步》(Giant Steps)这种难以理解的曲子的能力。我甘愿跑这种长跑。终点就是我爱约翰·科川。
但我同时也很疑惑:这真的好吗?
毫无疑问,科川是一个技艺奇才,据传每天练习超过12小时。但随着他从早期与迈尔斯·戴维斯合作的、相对保守的作品转向更为狂野的专辑《我挚爱之物》(My Favorite Things)和最后遗作、挑战性的自由爵士乐《星际空间》(Interstellar Space),他的音乐流露出传统的西式协调、结构和韵律。我并无对此烦心,我热爱科川的各种风格。然而他的后期音乐看起来无端随意,我不禁自问,长期以来我都在听些什么。
科川以自己首任妻子之名命名一首美丽又哀伤的民谣《奈玛》( Naima),然而这张唱片,真的像欧内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的散文、格温多琳·布鲁克斯(Gwendolyn Brooks)的诗句或者波丽吉恩·哈维(PJ Harvey)的歌词一样,以同样的方式传递着某种意义吗?或者说,尽管这首歌很美丽,它是否光芒微弱、毫无实在?科川只是随便唱唱,创造一种毫无意义的声音和愤怒?
这种怀疑并没有阻止我在大学学习爵士乐,多次亲手演奏爵士乐,虽然演奏得很烂。然而我到了20岁中期,爵士乐让我轻度惊慌。比如,听着昔日最爱的科川专辑《真爱至上》(A Love Supreme,1964),我发现这首歌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又一个该死的音符。
我能理解科川这样做是为了美感,毕竟我有个音乐学位,但是他的努力看起来毫无意义。《真爱至上》及其半生不熟的灵性是偶然和意外造就的美,就像落基山和DNA。当然,科川、钢琴家迈科伊·泰纳、贝斯手吉米·盖里森(Jimmy Garrison)和鼓手埃尔文·琼斯(Elvin Jones)组成的经典四重奏,听起来就像是自然之力,然而自然终归与人性迥然有异。同时,我欣赏过的其他艺术家,比如特罗尼尔斯·蒙克(Thelonious Monk)、孙·拉(Sun Ra),甚至艾拉·福兹杰拉(Ella Fitzgerald),他们看起来就像是边唱边作曲。
艾拉·福兹杰拉被粉丝称为“最伟大的歌手”,她的爵士乐款式多变,却传达着一种不变的精髓。(图源:画报出版有限公司Pictorial Press Ltd /艾拉米图库)
他们当然是杰出的歌手!这种爵士乐即兴创作的魔术被称为“独特美式风格”,它的地位如《圣经》般崇高,我很恼火这一点。被博物馆珍藏、被印在邮票上、被肯·伯恩斯(Ken Burns)拍成纪录片的音乐,听起来自命不凡。爵士乐其实懒不自惜又自大成狂,还老是依赖昔日桂冠和老调重弹的往日荣光,风光的日子早我几十年。至少巴赫(Bach)还费心写下一切。一旦《坐上那趟火车》(Take the A Train)、《大步》,或是嘎嘎叫的《沉思》(Meditations,1966)并没有传递任何信息,听这些专辑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持续戒断爵士乐。没有约翰·科川,数十亿的人照样生活美满,我也可以。我抛弃了爵士乐,转向一些量少意深的艺术家,比如约翰·李·胡克(John Lee Hooker)、香格里拉丝乐队(the Shangri-Las)、科尔·凯斯(Kool Keith)、黑旗乐队(Black Flag)、老虎乐队(Le Tigre)和大福里迪亚(Big Freedia)。每当我尝试在谈话和文章中解释我的爵士乐问题,总是会赢得嘲弄万千。去年,我在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社论,讨论的主题招来了成百上千的恶意邮件和批评,包括来自一个同事的野蛮回复。一些我怀疑(或知道)不如我熟悉音乐的人,坚持我愚昧无知,某种程度上我没有听到过对的爵士乐。他们的说法是荒谬的,无异于在说:“我知道你不爱泡菜,但你尝过我最爱的泡菜没有?”
其他人只是认为我的说法过于紧张:“你不爱爵士。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是个好问题。大概是因为我过去曾如此深爱过爵士乐,我不得不狠狠质疑它,以图弄明白我为何不再喜爱它。或者说,也许我不明智地认为一个文化评论员的沉思能将爵士推向更为敞亮的领域。也许有一天我会说:“我曾经喜欢过约翰·科川,后来我对他深恶痛绝,再后来我又重新爱上了他。”
我希望如此。做一个怀恨者一点都不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