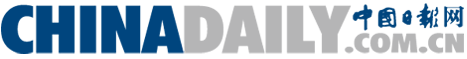在坦桑尼亚(Tanzania)的部分地区,女孩们都要被迫接受割礼(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FGM)。即便这一行为已触犯法律,许多女孩却无处求助,只得接受。现在,坦桑尼亚北部建立起了一间庇护所,为拒绝接受割礼的女孩提供保护。
“我的父母告诉我,我应接受割礼。因为我已经完读完小学,已经成年了。他们想我结婚嫁人。当我告诉他们我不想时,这激怒了我的父亲。”
维罗妮卡(Veronica,见上图),今年14岁。她语速非常快,快得都喘不过气了。
“我的父亲便开始打我,于是我决定逃跑。他还说我接受了割礼,我就会得到更大份的嫁妆。而家里那五头牛是要卖出去给我的弟弟交寄宿学校的学费的。”
“我当时对父亲说,‘首先,你得让我上中学,这样我才可能赚到钱,帮助家里其他人。’母亲的介入使得父亲非常生气,他对母亲拳打脚踢。我当时吓坏了,”她说道。
庇护所的一些女孩年仅10岁
在塞伦盖蒂地区(Serengeti District)“割季(cutting season)”每两年一次,每次持续六周。而维罗妮卡就是当时134个女孩当中成功逃到木谷牧(Mugumu)庇护所的其中一个。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被迫要求接受割礼的故事。割礼这一习俗源自当地库尔亚族的传统,是女孩们结婚的先决条件。
维罗妮卡是从学校了解到割礼的危险性和非法性,并威胁他父亲要把他告到警察局。而他的父亲立刻采取了行动。
“他把我关了两天,并外出找人帮我实行割礼。他们回来后,我骗他们说要上厕所。他们便放了我。我便逃到灌木丛里藏起来。但那里不时有动物出没,像鬣狗,也不是个安全之地。”
一位庇护所志愿者了解这件事后,把维罗妮卡送上了一辆前往木谷牧庇护所的公交。庇护所是依赖附近村庄的志愿者才得以发挥其作用。这些志愿者大部分是男性,他们曾见证割礼所带来的痛苦以及严重的健康后果,最为极端的案例中,女孩可能会因出血、感染丧命。
庇护所是由圣公会(Anglican Church)以及当地清真寺教会一同资助运作起来的。罗比·山姆威利(Rhobi Samwelly)是庇护所的管理人员,她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做好准备,就为了迎接第一个到来的女孩。
罗比·山姆威利的亲身经历激发了她建立庇护所的念头
“某个夜晚,我发现了一个哭泣着的女孩。看到她时,我非常震惊。当时,她身上连衬衣和鞋子都没有。她说她遭到了父母的毒打。”
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身上,我看到了她内心的绝望。罗比·山姆威利13岁时,无处可逃,被父母强迫接受割礼,大出血几乎丧命。
罗比·山姆威利意识到,这一地区需要一个庇护所来保护女孩们,但也无法预料究竟有多少人会来。根据设计,庇护所只能容纳40人。现在,女孩们两人、或者三人合睡一张床,地上还摆着床垫子。不过,看上去没有人对这拥挤产生不满。因为她们知道,能够逃到这里,已经是幸运。
索菲亚·玛克洪奴(Sophia Mchonvu)向维罗妮卡的父母讲述割礼
索菲亚·玛克洪奴乘着庇护所那辆破旧的四轮驱动车,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她此时正前往马斯涅村。她是一位庇护所里的社会工作者,专门去和住在庇护所里的女孩的家人进行磋商,警示他们割礼的危险性,并鼓动他们给予自己的女儿受教育的机会,而不是趁她们还年轻就把女儿嫁出去。同时,工作者们还会对女孩们回家后是否安全做出评估。
维罗妮卡的父母在他们的泥砖房外热情地接待了索菲亚。他们听到自己的女儿尚且安好的消息都非常高兴。
对于维罗妮卡的遭遇,她的父亲莫基利(Mokiri)解释道:“这都是源于更大的家族以及文化所带来的压力。”
他还说,他们已经意识到割礼的危险性。“我们不再遵循所谓的习俗规定。现在起,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家,我们尽责保护维罗妮卡。”他的父亲还承诺,不会强迫维罗妮卡的妹妹接受割礼。
即便如此,玛克洪奴认为,这还不是维罗妮卡回到家人怀抱的时机。
回木谷牧的路上,她还遇见了一位父亲和他15岁的女儿。他的父亲正想把女儿娜娅姬(Nyangi)带去庇护所。因为她的哥哥们试图让她接受割礼并早日结婚。在库尔亚(Kurya)文化里,新娘家会收到一头牛作为嫁妆礼。娜娅姬的哥哥们正想打这头牛的主意,来为他们娶妻所用。
娜娅姬
以及娜娅姬的父亲
除了娜娅姬还有她的哥哥们,娜娅姬的父亲还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住在一起。他告诉玛克洪奴,他已经和儿子们说了,割礼是一项陋习,他们不应该打自己妹妹嫁妆的主意。
他说:“我不想娜娅姬过早嫁人,起码也得28或30岁。我想她接受培训,成为一名护士。”
山姆威利决心保护像娜娅姬这类的女孩。“割礼和童婚在我国属非法行为。我不会蠢到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让这些女孩回家去。”山姆威利说道。
庇护所里最年轻的女孩博科赫(Boche)年仅10岁。她的腿上缠着绷带,只能蹒跚地走动。因她拒绝接受割礼,她的父亲用类似弯刀的短刀向她砍去。
“当时她的情况非常严重,已经无法走路了。志愿者和她一同到达这里时,我们便把她带去了医院。她在医院呆了两周,现在都快痊愈了。”山姆威利说。
塞伦盖蒂 “割季”的最后一周,许多被迫要接受割礼或说服去接受割礼的女孩开始走出隐居生活。她们一群群地走在土路上,掀起了黄棕色的尘埃。现在,她们已经成年了。她们穿行于一个个村庄,乞求钱财和食物。
在去其他村庄的路途上,山姆威利遇见了不少那女孩的父母和志愿者。她也曾停下来和一些女孩聊天,说笑,跳舞,唱歌。在谈笑间,她也借此机会告诉女孩们,她们仍面临着一些潜在的健康问题。
这对山姆威利来说也不是件易事。“我想让她们感觉到我与她们同在。但同时我又感到遗憾,因为这些教育对女孩来说,太迟了。”
塞伦盖蒂的地区执行委员约翰·亨杰维乐(John Henjewele)说道,虽这一做法属非法行为,但在“割季”,想要阻止割礼仍存在巨大的阻力。“问题关键是割礼是秘密进行的。警察要想确保每一户家庭都没这事发生是很困难的。”
这或许就解释了为什么“割季”结束时,塞伦盖蒂警察局的档案只有五件和割礼相关的案件。另外,还有一些当地领导人也不愿加入反割礼的行列。
亨杰维乐说:“实际上,由于受到文化和长辈们的束缚,使得该地区的政客很难张口声援,反对割礼。”
亨杰维乐来自坦桑尼亚的南部,那里并没有所谓的割礼,所以相关言论并未受到约束。他支持木谷牧庇护所的做法,并对女孩们所接受的割礼教育感到自豪。正是因为教育,使女孩们向威胁自己生命的行为说“不”。
但并不是每个女孩都能安全到达庇护所的。“我们接到一个电话,说村里七名少女藏在林子里,”山姆威利说道。她们从家里逃出来,试图躲避接受女性割礼。
“我们立刻派出车辆去接他们。不幸的是,车辆破旧,半途抛锚,我们没有及时赶到。女孩们的家人找到了她们的藏身地。七个女孩儿中,五个没能躲过这一刀,只有另外两个被解救了,并去到了木谷牧的庇护所。这让我非常痛心,我没能及时解救她们。”
现在,塞伦盖蒂的“割季”已经结束了,超过一百名女孩已经从庇护所回到家了。因为她们的父母已经签订了一份管制声明,承诺会保护她们的女儿,远离割礼。
维罗妮卡和娜娅姬还是和山姆威利一起留在庇护所。维罗妮卡正在学裁缝和烹饪技术,而娜娅姬则去上中学。虽然上中学在坦桑尼亚并没硬性要求,但这也是许多小孩梦寐以求的。另外还有30名女孩也留在了庇护所。而博科赫则跟她妈妈一起生活,她的父亲已被警察逮捕。
据悉,在为期六周的“割季”里,塞伦盖蒂地区已接受割礼的女孩中就有超过15名因割礼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