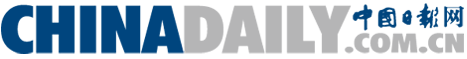阿旃陀石窟拥有惊人的财富,是个被遗忘了近1500年的佛教圣地。乔纳森·格兰西为你拨开重重迷雾,一窥阿旃陀石窟的真相。
1819年,一次偶然让阿旃陀石窟(The Ajanta Caves)重现人间。阿旃陀石窟位于孟买(Bombay)东向450千米(约280英里)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 state),隐于深山密林中。阿旃陀石窟群岩壁呈马蹄形,共30窟,包括佛殿及僧院,其精雕细琢,浑然天成,宛若魔咒,令人着迷。
早于公元500年,阿旃陀石窟诞生于世。然而1000多年间,这个艺术瑰宝、宏伟建筑和冥想圣地被遗弃在历史长河中,除却野生动物,昆虫,洪水,连绵落叶,或许还有本地比尔山民,这里人迹罕至,默默无闻。1983年,阿旃陀石窟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年轻的骑兵军官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当时正追猎一只猛虎,偶然发现了瓦格拉江(Waghora River)(又名虎江)上高处一处人造洞穴的山口。史密斯纠集队伍,手持杂草火炬,进入了洞穴。他眼前展现的是佛殿完美的拱形穹顶和柱廊,还有墙上模糊的壁画。穹顶下一尊佛像静坐于垛状神龛或佛塔前部,合十祈祷,跳脱时间之外。
阿旃陀洞窟于公元5世纪淡出世人视线,直到1400多年后才重现人间(图源:Dinodia图片社/Alamy图库)
史密斯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一尊菩萨像上。菩萨,是诸佛涅槃(Nirvana)或是天人合一前的身份之一。自那之后,阿旃陀石窟一举成名,成百上千的游客来此留下他们的名字。这个典藏着部分最古老、最优秀的佛教艺术品的艺术画廊,成为引人入胜的旅游胜地。
史密斯发现洞窟的消息迅速传播。1844年,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Cave Temple Commission)授权梅杰·罗伯特·吉尔(Major Robert Gill)在帆布上临摹复制壁画。这只是发掘和保存佛殿及僧院系列措施的第一步。整个石窟群的雕凿可能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公元前1世纪至2世纪间,雕凿5窟佛殿;第二时期为公元5世纪,雕凿25窟僧院。
吉尔的工作环境真的很艰苦。不仅天气经常炎热难忍,而且此处民风剽悍,比尔人凶猛悍戾,无法忍受外人入侵,无论是印度人、莫卧儿王朝,还是19世纪的英国军队。
消逝于时
通往石窟的石阶早已消失无踪,借助登山绳和梯子,吉尔和其他游客登上石窟。浮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建筑,内部雕塑和壁画美得令人屏息。在这里,僧侣们端详着成千上万光辉肃穆的壁画,了解公元6世纪成为佛陀普度众生,受几亿信徒追随之前,印度王子悉达多·乔达摩(Siddhartha Gautama)的生平。
魅力非凡的王子公主、动物、宫殿、丝绸、珠宝、性爱和穷尽奢华的世俗生活等感官表象活跃于佛陀的壁画中间。某些壁画冲击了维多利亚时代伦理感情观,至今仍不断受到宗教狂徒的谴责。这些壁画在印度艺术家眼里,描绘的是自然繁殖的欢愉和圣洁美丽,宗教狂徒显然无法理解这一点。
洞窟内部排列着色彩斑斓的壁画,某些壁画为适应墙壁的形状被拆分为几部分(图源:伊凡·弗多温(Ivan Vdovin)摄/Alamy图库)
这些壁画和公元1世纪的建筑和希腊古典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切并非巧合,而是公元前4世纪随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传播而来的希—印文化的铁证。希—印文化源自希腊王国,随着商队路线,自地中海始,途径波斯和阿富汗,为印度带来阿旃陀洞窟,然后延伸到遥远的中国和日本。
伦敦南都西德纳姆(at Sydenham)水晶宫印度庭(the Indian Court of the Crystal Palace)展出了27幅吉尔的油画。然而在1866年,其中23幅油画葬身火海。后来,吉尔携带新型照相机和画刷,重投临摹事业。同时,皇家亚洲学会于1848年成立的皇家石窟寺委员会(the Royal Cave Temple Commission)促使了印度考古研究机构(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的成立。人们对阿旃陀洞窟的关注越来越多,胆大无畏的专家和宝藏猎人也不断出现,他们之中某些人的劣行可不单单限于在雕像上留下大名:他们从墙上挖下了壁画,导致壁画碎成了粉末。已知仅有寥寥几幅壁画能完整无缺地离开阿旃陀洞窟,其中一幅现今位于美国,由波士顿美术博物馆(the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护理。这幅壁画曾于1924年被伦敦索斯比拍卖公司(Sotheby’s)以1000欧元出售。
孟买政府1872年曾授权孟买艺术学校(the Bombay School of Art)校长约翰·格里菲斯(John Griffiths)临摹阿旃陀洞窟的壁画。格里菲斯带领学生临摹了300张画作,还只是1885年伦敦帝国学院(London’s Imperial Institute)烧毁的临摹画作量的三分之一。1909年,妇女参政权论者兼艺术保护人赫林翰伯爵夫人(Lady Herringham),在加尔各答艺术学校(Calcutta School of Art)的协助下开始了进一步的壁画临摹。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印度艺术史家吴拉姆·亚兹达尼(Ghulam Yazdani)做了一个阿旃陀洞窟的全面的摄影研究,并分成4册先后于1930年至1955年间出版。
同年,火灾中幸存的格里芬斯临摹作品被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收藏。之后半个世纪人们都难以见到这几幅作品,它们渐渐淡出人们记忆。直至2005年8月1日,它们才重见天日。
探索理解
自1999年,印度考古研究机构成员拉杰德奥·辛格(Rajdeo Singh)采取日本传入新方式,加以印度艺术家精妙的透视手法、绘影方式和其它3-D技术例如阿富汗的青金石等晔石的运用,揭示公元1世纪许多壁画浓烈的色彩和纯粹的美。
为迎合希望身临其境的游客所建造的一组复制石窟(图源:罗伯特·普雷斯顿摄/Alamy图库)
他们这一精细的复原工作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过去200年间从未能得到解答。过去的艺术家是怎样在这些佛殿、僧院黑暗的壁凹里面准确运用颜色,画得这么好的?同样,在约公元460年到公元500年哈里森那王(emperor Harisena)统治的伐卡塔卡王朝(Vakataka dynasty)中,这么多建筑家、石匠、雕塑家和画家是怎样在受到商人和朝臣的雇佣下,不失创意去建造这个辉煌的洞窟的?还有,在伐卡塔卡王朝及其对佛教艺术的支持覆灭前的短短几年,阿旃陀洞窟占地如此宽广,它真的可以作为一个安静的冥想圣地吗?
过去两个世纪的考古冒险试着去解答这些问题,去揭露、记录和保存这个佛教艺术创新盛典。这些艺术创新极大地提高了阿旃陀洞窟的名望,不断吸引着游客前来一窥芳容。2013年,孟买本土设计师拉凯什·拉索德(Rakesh Rathod)创造了4个复制洞窟,置于离岩壁4千米(约2.5公里)外的游客中心开放参观。拉索德意在减少前往宝贵的佛殿和僧院的游客数量。
然而复制洞窟未能达到原定目的,很明显游客更想去真正的洞窟,尽管如今很多游客长途跋涉,却沉浸在阿旃陀途中的集市和小吃摊中。
但是其中一个洞窟中那尊安详的卧佛雕塑,那尊冬夏至日光照耀着的祷佛像,那摄人心魂的建筑和扣人心弦的美丽壁画将阿旃陀洞窟捧到了世界焦点的顶峰。阿旃陀洞窟也许是一块旅游吸金石,然而多亏文物保护者世世代代的努力,阿旃陀洞窟得而留存,人们方有机会在此一窥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