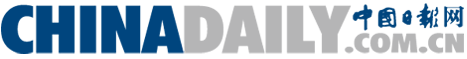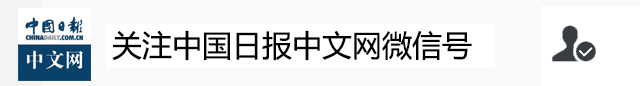街道之下,是“鼠族”的隐秘聚居地
每日清晨,中国首都北京的地表之下,一场“变身”正在悄然进行。在这个没有阳光和新鲜空气的世界里,人们从没有窗子的房间里起床,到公厕倒便盆,然后花五毛钱洗五分钟澡,爬上水泥梯走向外面的世界。他们从这个城市里居住条件最差的居民“变身”奋斗者,一点一点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这群约有一百万人的北漂族,被称作“鼠族”,因为他们安家于地下常年阴湿又拥挤的小房间里。这些小房间比地面上同等条件的房子都要便宜。政府明令禁止出租地下室和战时遗留下来的防空洞,所以严格来说,大部分的地下住所都是违法的。但在中国,凡事皆有灰色地带。地下住房有着巨大的市场——租金几乎是地面上同等条件住房的一半——因此,当地政府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大部分的地下住户都是年轻的外来人员,他们希望在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城市里找到立足之地。北京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中心,还是一个生活方式不断变化的文化和商业中心。他们中有演员也有清洁工,有发型师也有洗头小妹,有新婚夫妇也有姻亲,有佛教徒也有基督教徒。许多人的故事都非常具有戏剧性,甚至还有人当过匪徒。比如这位白手起家的27岁小伙卫宽(音),就经历了从小罪犯到保险推销员的转变。他还曾当过快递员、葬礼歌手、足部按摩师和澡堂员工。
保险推销员卫宽说,他住在地下室公寓是为了省钱做其他事情。最近,他给自己买了一套定制的羊毛西装。卫宽希望能够攒下足够的钱买一辆车。
“我很努力,因为我不想做穷人,”在和另外九人合租的约28平方米的公寓里,卫宽说,“我的许多同事都住在地面上,但我觉得不必住得那样舒服,住在这里更能激励我努力工作。”卫宽现在月收入达三万元人民币——这与他以前800元的月收入已是天壤之别了——他说,他计划在春节的时候搬出去,也就是二月份左右。
这些地下房屋的存在与两个历史事件有关联。一是美苏冷战,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正与前苏联竞争,希望成为东盟的意识形态主流。1969年,两国爆发了阿穆尔河(Amur River,即黑龙江)边界战争,同年,毛泽东命令人们“挖深地道”以防范前苏联空袭。当时,北京有三十万人参加了这场运动,挖了约两万个地下防空洞。
然而几年后,毛泽东去世,坚持经济第一、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对他的强硬路线进行了调整。随后防空洞商业化。人民防空办公室下达指示,防空洞必须创造利润。根据负责这项工程的高级官员的回忆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有800个地下公寓、地下超市、地下电影院和地下旱冰场。1996年,政府通过了一部关于新建建筑的法律,其中就包括地下防空洞,使得这一转变得以正式定型。根据这一法律,地下民防庇护所也可作商用。这就促进了地下商业性房屋的增长。过去这些年,政府部门把这些空间承包给私人经营谋利。
北京东区的一处地下住所
图为北京东区一处地下住所的平面图(非等比例)。由上图可以看到本文中五位受访者的房间位置。左边是街道进入地下住所的入口,气闸门就在入口处。中间就是当初用作防空洞的地方。
图为另一位地下住所住户正在查看地下平面图
北京成为地下房聚集的中心,也有部分地理因素。北京邻近中国北部的沙漠地带,除了夏季几个月较湿润,其他时候都非常干燥。这就让地下住所与靠山地区的传统洞穴房屋相似——冬暖夏凉,且要比住在嘈杂的地面上安静得多。
第二个重大历史事件就是城市化。城市化让中国大部分城市迅速扩张。北京人口由1995年的九百万增至2013年的约两千一百万,其中八百万为外来人员。加之许多外来人员都是非法居住在大城市,这就增加了廉价房屋的需求量。他们既没有北京户籍,也没有城市户口,因此既不能合法居住,也无法申请低收入住房、当地学校以及其他福利。既然无法定居在北京,他们就会选择较为低廉的住房。
北京也有其他的低成本住房,但多在边远的郊区,或者是六到十个人合租一间类似于宿舍的房子。在地下,大部分人会租一个约4到9平方米的单人间,月租金约为400元人民币,基本上是地面同等住房的一半。这就让外来人员在城市核心区域有了一个生存空间,同时也方便他们上班。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教授安妮特· 金( Annette Kim)与北京大学的卢彬(音)教授一起调查了3400间地下公寓。她说:“当然,没人想住在地下,但是一些人对居住地点的远近有强烈的需求,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经济适用房工程都在远离城市的区域,因为只有在那么边远的地方,人们才付得起房租。但是人们又不想住那么远,那样通勤路程太长了。”
尽管具有这些优势,住在地下的人还是会觉得见不得人。一些外来人员表示,他们还没告诉家人,或者推迟了几个月才告诉他们。张曦(音)是一位有抱负的演员,他说:“我父亲来北京看我的时候,见到我住的地方,他大声说:‘儿子,不要这样子!’”
张曦:蒙古演员的大梦想
严格的条例和规章制度加深了他们的被遗弃感。一些地下室贴着告示,要求住户不要把寝具拿到地面通风,哪怕是晒太阳也不行。
世界范围内,城市正变得越来越密集。鉴于此,安妮特·金觉得北京的“地下城”并不是冷战的遗物,反而开创了亚洲人口密集城市的住房新形式。
官员们对地下住房也是五味杂陈。过去的两年里,北京市政发布的信息可谓自相矛盾。2011年,他们表示,出于安全隐患考虑,如火灾或洪灾,将于2012年禁止防空洞作住房使用。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似乎有悖于北京现代化的城市形象。
“我们从未允许将防空洞作为居住用地,” 北京市民防局副巡视员许金宝说,“但随着北京人口规模越来越大,人们开始涌入地下公寓。”
然而,这些改造性住房和其他地下住房也可以是解决城市住房危机的可行方案。“一些地下住所已经被拆毁,但是我觉得这些住房仍有着巨大的需求,且未来的需求量只会增不会减。”北京工业大学专门研究地下住房的社会学家李俊复(音)说。
地下住房可能会继续保留的另一个原因,是地下住房管理者们签署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许多管理人员自身也是外来人员,他们倾尽毕生积蓄安装了闭路电视,达到了防火安全要求,隔出了独立小间。早前,有关部门曾尝试关闭一些地下住所,却引起了公众的抗议,这在中国是一种罕见的现象。
上图的张海海(音)今年26岁,他与女朋友合租了平面图上的4号房。出租房长2.2米,宽2米,还有一个小通道。张海海在一家广东菜馆当厨师,空闲时间他喜欢在笔记本电脑上打打电子游戏,看看电影。
图为49岁的段树梁(音)与他50岁的妻子刘星儿(音),都是洗碗工人。他们的房间是平面图里的3号房,长2.4米,宽1.9米。老家的一小块地被征用后,他们来到北京。张海海和他的妻子都很看得开。“我们上班的时候不戴表,这样我们就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了。”段树梁笑说。
李俊复估计,有约百分之五的北漂族居住在地下。尽管这比中国一些媒体报道的要少,但安妮特·金认为这一数据是准确的。李俊复说,最让他震惊的是,“鼠族”并非走投无路才住在地下,而是精打细算地为未来做出的暂时性牺牲。“我发现许多人都希望有一天可以买自己的房子,或者是住到地面上,”李俊复说,“他们都十分乐观,而且积极向上。”
摄影师沈琦颖(Sim Chi Yin)给超过百位地下住户拍了照片,并根据长达五年的调查得出的结果,做了一个多媒体展示。虽然大部分地下住户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处于经济圈的底端。以下就是他们中一些人的故事,在北京挣扎于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典型故事。
“鼠族”成员
陈拉秀(音):清扫地铁的奶奶
陈拉秀意识到了一点:生活在北京比务农好。50岁的陈拉秀来自贵州六盘水,一个煤矿小镇。虽然她家在六盘水有约6亩地,但仍不足以支撑她抚养三个儿子成家。几年前,她的小儿子搬到了北京。去年初,陈拉秀也和丈夫一起来到北京,还没想过要回去。
张鑫文(音):现代版梵高
李扬(音):地下渔民
李扬有着专业汽修技工的背景,但他现在住在地下。他希望成为一位权威的“飞蝇钓”(广泛流行于欧美的溪流钓法,以钓取凶猛掠食性鱼类为主)专家。
与住在地下的大部分居民不同,李扬来自通州——距离市中心32千米的北京郊区。他以前在家里的农场里做点零工,后来慢慢开始对“飞蝇钓”着迷。2012年,他在一个钓鱼比赛中胜出,并得到了中国钓鱼电视频道的主编的会见。从那以后,他一直在给这个频道写信,希望可以出一本关于这个项目的书,并以此谋生。
郭晓龙(音):“鼠王”
郭晓龙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工作地点都是一些不怎么起眼的夜总会和卡拉OK酒吧,当地人称为KTV。郭晓龙今年40岁,是北京东部郊区6号线下的地下室经理。他现在管理着72间房,近100名住户。他自己的房间是平面图上的5号房。
杜秀艳(音): 给儿子筹老婆本
杜秀艳在北京一家东北菜馆里包饺子,洗碗,煮疙瘩汤。从两年前来到北京,她就一直在琢磨:能不能赚到足够的钱给儿子娶老婆呢?
昌湾乐(音):初来乍到就被骗
昌湾乐从老家河南安阳来到伟大首都北京。刚下火车,他的梦想就受到重重一击:一位无牌照的出租车司机收取了他近十倍的车费。他说,这让他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极差。
许俊萍(音),周海林(音),周征迪(音):简单生活
对于许俊萍来说,北京及其地下的临时住所都像是她的庇护所。8年前,46岁的许俊萍从山西来到北京,她喜欢地下安静的生活和北京的简单生活。与在乡下的家中不同,她在北京来去自如,不必顾及邻居和亲戚。来到北京后,她在一个集市贩卖佛经、香烛和护身符,也因此成为了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夜里,地下住房就是她的庇护所。
刘浩(音):城市摄影师
刘浩的房间上面,是一栋中产阶级居住的复式公寓。那里的住户会到星巴克买咖啡,到无印良品等高档日本百货商店购物。公寓后面有一个棚子,打开棚下的门,下楼梯,你就走进了刘浩的世界——一位初露头角的作家、诗人、摄影师和电影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