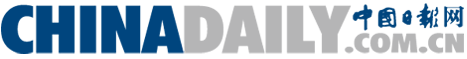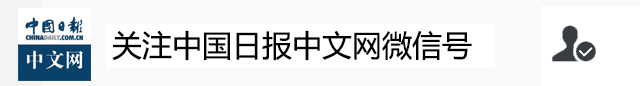这位18世纪激进的浪荡之徒已在我们的文化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无所不在——但他为何还会令我们感到恐惧?贾森·法拉戈如是说。
1783年,被囚禁的萨德侯爵(Le Marquis de Sade)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杀了我,或者接受我,因为我不会作出任何改变。”对于这位18世纪最极端的作家来说,结局只能是这二者之一。11年的漫漫牢狱之灾,此时还只过去了一半;然而萨德是不可阻挡的,他不会为了摆脱禁狱之苦而放弃自己的原则,或是扭曲自己的品味。因为一旦背离了自身的真性情,哪怕只是一点,他就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
如今萨德得以“重见天日”,但他依然受到人们的误解。不过2014年12月在巴黎举行的两场展览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世人得以重新审视这位欧洲文化史上最具黑暗影响力的人物。巴黎奥赛博物馆在月底举行了名为“萨德:攻击太阳”的展览——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展览秀:在这里,透过一面特殊的棱镜现代艺术史将会被重新解读,而这面棱镜就是萨德激进的文学作品。展览期间,巴黎书信手稿博物馆也推出了萨德的书信和作品展;展出的物品包括《索多玛120天》的手稿,这可是一部极其大胆而令人反胃的作品。这两场展览都能够启发观众去更加深入地思考萨德生活的时代,以及我们生活的时代;而他们会发现这两个时代是多么地相似。
18世纪孕育了两个孩子——法国和美国。然而即使是在法美,人们对于18世纪的认识都有些片面化,都有一定的欺骗性。启蒙运动点燃了理智、理性、科学和人文的火炬,但这并不是18世纪的全部内涵。200年前的12月,萨德离开了人世;而他毫无疑问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很崇拜卢梭——尽管狱卒们不允许他读卢梭的著作。他先发制人,火力全开(萨德会喜欢这个比喻),向理智和理性的首要地位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崇尚一切反叛的、极端的事物,反对当时盛行的人文主义——正是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这些思想激怒了那个时代“伟大而美好”的人物。然而这些极端反叛的声音却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响彻了整个艺术、文学和哲学的世界。
罪恶原则
当拿迪安·阿尔风斯·法兰高斯·迪·萨德(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de Sade,萨德全名)出生于1740年,他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人。他是一位贵族,却也是一位坚定的左派人士;他是法国大革命中国民公会的代表,曾在恐怖统治期间放弃了他贵族的名号。他的部分小说被认为是文学史上最具挑逗性的作品,但他也写过一些乏味的传统小说,而这些小说毫不淫秽。当然,他对于更加粗野的性交方式有着强烈的兴趣:“sadism”一词,字义为“性虐”就是由他的名字来命名的;然而一项关于18世纪文学的粗略调查显示,性交并不是这个时代文学特有的主题。伟大的性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经说过,性虐行为并不是“与爱神厄洛斯同时出现的”,而是“在18世纪末期产生的一种大规模的文化现象”。
同他的前辈们伏尔泰和卢梭一样,他的小说既可以看作是用来消遣的闲书,也可以看作是发人深省的哲学论文。即使指着他最离谱的小说《索多玛120天》(120 Days of Sodom),人们也不能说他是一位真正的色情作家。《索多玛120天》的初稿描绘了大量有关切割、破裂、杀戮、流血和死亡的情节,但却丝毫未涉及到性。然而他最好的小说《茱丝蒂娜》(Justine)却讲述了一位放荡的牧师如何向少女的身体里插入圣餐饼而玷污她贞洁的故事。这本小说在法国社会恶评如潮,并不是因为它过于色情,而是因为它描绘一幅漆黑的道德图景。在这图景中,虐待他人不仅仅是可以接受的,还很可能是种美德。萨德同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一样坚定地认为每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并将责任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在萨德看来,所谓真正的道义准则,它必然包含了一种追求——跟随内心深处最黑暗、最具破坏性的激情直到天涯海角,即使牺牲他人性命也在所不惜。(给不熟悉萨德的人提个醒:萨德并不排斥谋杀,尽管他坚决反对死刑。因激情而杀死一个人是一回事,但通过法律为杀人正名却是野蛮残酷的行径。)
他写道,“我们严辞咒骂激情,但殊不知正是激情点燃了哲学的火炬。”对于萨德来说,拥有卑鄙残酷的欲望并不是越轨的行为。这些欲望是人性的根本,是人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说,启蒙思想家们所推崇的理性只不过是人们内心深处欲望的一种副产品罢了:人类是受欲望支配,而非受理性支配。高贵是一场骗局。残酷是自然的。不道德是唯一的道德,罪恶才是唯一的美德。
影响恶劣?
萨德不仅在写作方面偏走极端,在个人生活中也是放浪不羁。他惹出了一大堆麻烦,为此他人生中的三分之一都是在监狱和精神病院里度过的。(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道,“人生这场戏,我的幕间休息实在太长了。”)在他于1814年去世以后,他的书很快遭到了封杀。然而就在作品蛰伏期间,他所描绘的黑暗道德图景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当画不了西班牙王室成员的微妙讽刺画像时,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就致力于创作疯狂的版画系列——随想曲、战争的灾难、前一夜的梦境——在这些系列中,残酷战胜了美德,而无意义战胜了理性。在他最著名的版画里,一个人正打着瞌睡,也许正是画家本人,他被自己噩梦里的野兽搅得心神错乱。这幅画的说明文字是“理性入眠,怪物因生”。福柯将戈雅的画作,尤其是他那严峻而极具讽刺意味的随想曲系列,看作是萨德著作的天然对应物。他表示,在两者中“西方世界都看到了通过暴力来超越自身理性的可能......在萨德和戈雅之后,非理性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决定力量之一。”
在萨德勾勒的道德图景中,人类不受理性的支配,身体会在极端的状态下得到释放。他的想法影响了19世纪早期的许多艺术家,特别是欧仁·德拉克罗瓦( Eugène Delacroix )和杰利柯·西奥多( Théodore Géricault)。但他的作品却鲜为人知。在世纪之末,“神侯”才真正得以重新发掘。对于一些人来说,萨德的作品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对性的猎奇心理。(维多利亚时期诗人查尔斯·斯温伯恩十分崇敬萨德,他曾以笔名写过一篇冗长乏味的讽刺史诗,讲述小男孩们被鞭打的故事。)然而,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们看到了萨德更大的价值:他是一位哲学家,注视着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
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在《恶之花》( The Flowers of Evil)中写道,“我是伤口,也是那锋利的刀刃!/我是巴掌,也是那挨打的脸颊!”《恶之花》是最早将萨德原则重新运用到文学写作的作品之一。萨德的性生活是完全公开的,弗里德里希·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的性生活却是完全保密的,而尼采显然欠了侯爵一个很大的人情。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首次使用了“超现实主义”这一说法,他也编辑了萨德的第一部作品全集。萨德的作品里有关性和暴力的场景往往都不符合解剖学原理,因而成为了许多超现实主义者早期灵感的来源。
但并非只有他们。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讲述了一位殖民地官员在刚果发疯的故事,它本质上是一部萨德式小说。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颓废大作《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也是一部萨德式小说,小说的主角是一位教授,而他内心里唯一真正的欲望却是社会的道德禁忌。若是没有萨德的启发,很难想像弗洛伊德还能提出自己独创性的学说;正是萨德在早弗洛伊德的一个世纪以前指出了人性的核心即是性欲。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导演了惨不忍睹的《萨罗》——一部根据《索多玛120天》改编的影片;帕索里尼也被认为是萨德最伟大的电影学生。萨德也深深影响了各种大相径庭的传统电影形式,从大岛渚( Nagisa Oshima)的《感官世界》( In the Real of the Senses )再到约翰·沃特斯(John Waters)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垃圾电影”。
他无所不在,但他依然使我们感到恐惧。为什么?因为萨德提醒我们,任何冷静客观的分析都是无用的;身体与头脑同等重要,而理性必须要服从更深层、更可怕的冲动。甚至他那些所谓的崇拜者们都觉得无法忍受——在菲利普·考夫曼(Philip Kaufman)的2000年电影《鹅毛笔》( Quills)里,由杰弗里·拉什饰演的萨德被美化成了一个捍卫守法的言论自由的殉道士(电影里还配有一段荒谬和绝对虚构的残缺片段;实际上,萨德是平静地死去的)。但是,萨德代表的是极端,而不是自由。他是时代的先知。如今这个世界正不断突破政治、经济和生态的极限,我们会发现他对于人性的黑暗定义看起来愈发地冷峻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