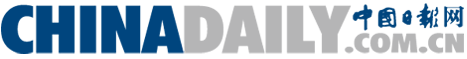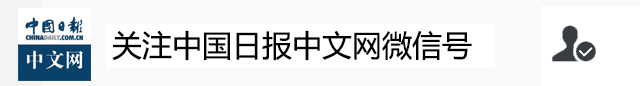2015年2月6日,雷鬼音乐超级明星鲍勃·马里本该迎来七十大寿的生日。他的朋友薇薇安·高德曼(Vivien Goldman)探寻了这样一个兢兢业业的活跃分子怎样逐渐变成无忧无虑聚会代表的过程,向其长久不衰的影响力致敬。
“我真的没有说过别人坏话,因为我挺看得开,”鲍勃·马里曾经告诉我。“那是无知散漫的人的标志。我宁愿只是了解情况,弄清楚事情真相,辨别是非。”
鲍勃·马里敢于选择立场,不害怕站在道德权威上唱歌。随着世界各地举行许许多多的活动来纪念他曾经所参加过和歌唱过的斗争,我问自己:如果鲍勃能活到70岁,那他会怎么庆祝生日呢?他会写什么歌呢?
当美国国内警察不断杀害黑人男性同胞促使了多民族发起的“黑人也是人”的抗议示威活动,鲍勃演唱了《没有女人,没有哭泣》(No Woman, No Cry)和《约翰尼是个好人》(Johnny Was a Good Man);当宗教极端主义发动恐怖袭击,而残忍暴行隐匿时,鲍勃演唱了《我们和他们》(We and Dem),“我不知道我们和他们将如何解决问题”; 当北极融化、非洲湖泊干涸,我们都渴望 “自然的奥秘在空中扑面而来”,一致同意拉斯特法理派成员(Rastafarian)所谓的“巴比伦”制度——贪婪的资本主义制度或是高压政权——实际上是“一个吸干受难者鲜血的吸血鬼,”。然而,时至今日,鲍勃·马里常常以深受年轻一代音乐爱好者崇拜的偶像形象出现,就像当初莱德贝利(Leadbelly,1888~1949,美国民谣的传奇人物)于我一样,是一位富有魅力却远在天边的偶像。
我在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教授一门课程,名叫《马里与后殖民主义音乐》(Marley and Post-Colonial Music)。实际上,当你教授你认识的人时,会发生一些离奇的事。其中最稀里古怪的?比如《星期六晚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在电视上拿我这一门课程开玩笑。赛斯·梅耶思(Seth Myers)面无表情地说道,“纽约大学教授关于鲍勃·马里的课程命运不济,只能安排在早上8点钟。” 更有趣的是,我不明白这个笑话的意思。(我的学生也不明白,直接发邮件问我:“我们真的要那么早上课吗?”)这个笑话的笑点在于他们认为鲍勃·马里吸大麻比他的音乐更加出名,同时也暗示他的粉丝一定是懒鬼。不过,上我这门课的学生是顶尖学生,而且我所知的鲍勃·马里也是一位非常与众不同的人。对他而言,大麻是长矛,是工作道德的利器,无懈可击、永不停息、甚至是残酷无情。业内人士经常笑称鲍勃·马是“第一个坐上巴士,最后一个离开演播室的人”。这是他领导力的一部分,不过,这并不是他在大部门人们心中的形象,尤其是在美国。
美国一流行网站的音乐编辑近来告诉我,他想播放马里的音乐,而中西部大学的广播台程序员们因此而嘲笑他,他们认为这明显是行为怪异的表现。
现在如果广播真的播放鲍勃的歌,那也是舒缓柔和的歌曲,而非闻名的愤慨激昂的歌曲——收录在如《传奇》、《金士顿12》(Kingston 12)专辑里。《出埃及记》里面既有对抗斗争的歌曲,又有阳光普照高地的歌曲,我的学生们学习《出埃及记》以及它的排序时,意识到虽然他们都听过愉快甜蜜的爱情歌曲,但是没人听过斗争的歌曲,而鲍勃的歌就是这样。但是有人批评鲍勃《出埃及记》的曲风与柔和甜美的《日本榧树》(Kaya)类似,不过,我仍然记得鲍勃唱到“我要唱同样的歌多久”时,他那疲惫的笑容和轻微反抗的语气。
“如果我身后有更多的人,我会更加激进!”他坚持道。但是鲍勃也很高兴能达到一个新高度。他不想只被视为一位士兵,因为“你有时候得想起女人,唱像《调暗灯光》(Turn the Lights Down Low)一样的歌曲。”他从未想过有一天曾经的斗士,在民众的心目中变成一个大众情人或是聚会上自我感觉良好的花花公子。但正如鲍勃在音乐中所唱的,“我喜欢的是发展的过程。”
经常有人问我鲍勃·马里是否真的是一个正直勇敢的人。确实是,他并非完美无缺,但他在努力实现理想,真诚无比。他曾经对我说,“真理就是真理。有时候你得做出牺牲。你不能总是躲躲藏藏,总得吐露真理。如果有人因为你说出了真理而伤害你——那么你至少说出了真理。”
我与鲍勃这些交谈发生在1976年,也是他人生中的关键时刻。1975年,我在环球唱片公司(Island Records)当了他7个月的公共关系人。队里的部分成员帮助他在英国凭《没有女人,没有哭泣》一炮打响。接着,我开始经常在路上或是在家写关于他的故事。有一次任务中,鲍勃邀请我去他金士顿希望路的家中,我们进行了一次有着命运转折的亲密交谈。
我录下了那些日子里我们的部分对话。那些对话有着浓浓的弦外之音,我并不能马上明白其中的意思。有一次他说,“牙买加是一个可笑的地方。人们非常喜欢你,以致他们想要杀你。”我以为他是言过其实。在演播室录制他最阳光的歌曲之一《微笑牙买加》(Smile Jamaica)时,他看起来焦虑万分。他告诉我,“牙买加人必须微笑。这儿的人们烦恼太多了。” 当天晚些时候,他在希望路的院子里漫不经心地弹吉他,作有关大鱼吃小鱼的词,后来出现在《羞愧》(Guiltiness)里。鲍勃预测道,残忍自私的掠夺者会“不择手段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果然,那天我离开希望路去伦敦后,四个政治激进的枪手闯入了希望路避难所,向鲍勃、他的妻子Rita和经理唐泰勒(Don Taylor)开枪后逃逸。之后,鲍勃和哭泣者乐队(the Wailers)逃亡到国外一年半。
在我研究自己写的《出埃及记的书》( The Book of Exodus)时,有个黑社会头目的妻子,也是拉斯特发力信徒透露称,她的丈夫发现了枪杀鲍勃的阴谋,曾打电话警告他。尽管鲍勃当时向那些恶毒势力暗示,他对谋杀自己的计划心知肚明,甚至在开枪前,他就知道枪杀即将来临。两天后,他仍继续举行了《微笑牙买加》音乐会,意在1976年12月大选之前鼓舞团结人民。大学老师和政客都想拉拢鲍勃到他们那边。12月5日,鲍勃在台上表演,手上还缠着绷带,手臂里还有一颗永远存留的子弹;拔掉子弹的话可能会使鲍勃以后再也无法弹吉他。所以他很清楚选择政治立场的后果,但是他仍然义无反顾。这就是勇气。
鲍勃有着求真务实的世界观,有些人说那是愤世嫉俗。1976年拉得布·罗克丛林(Ladbroke Grove)老街的诺丁山嘉年华发生暴乱时,我正巧在金斯顿(Kingston)与他交谈。我气喘吁吁,告诉他取缔嘉年华计划的最新消息,静静等待他的回复。他的回答深谋远虑,同样适用于今天更加大型的冲突,他如此说道,“我们无法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引起这些问题的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些事情是有计划的,因为人们一定是变得太革命,或是他们知道得太多。”他从来没有忘记牙买加人的根本,“我们都曾是从非洲运来的奴隶,这是事实。这是真真确确的。所以那些有钱有权的人只想让我们依然当奴隶。如果你谈论这些的话,”他继续道,带着不同寻常的嘲讽,“他们说你在谈论政治。他们能够天南地北任其高谈阔论,而一旦我所认为的方式有违于他们,那便是死路一条。遵守也是死路一条,因为如果你遵循他们,你就完了。”
一位将生命托付给信仰的音乐家,在歌曲中传达自己的心声,甚至小孩子都能哼唱他的歌曲?这种说法今天听起来近于怪谈。既然音乐家都不再像他们曾经那样奋起反抗,那么鲍勃·马里的信息意味着什么?
终其一生,鲍勃是一个努力控制其音乐产出的艺术家。早期他任劳任怨,任制作人宰割,马里在生命的尽头,他与一个跨国公司谈判,筹集资金建立了塔釜·龚(Tuff Gong)唱片公司。他预计这将成为很多受尊敬牙买加音乐家的集体,但现在他的音乐传奇在不同的一代人手里。马里逝世后的市场取得空前成功,他的遗产在所有音乐家中最赚钱。
他没有留下遗嘱,逝世后几年,他在《唯一的爱》(One Love)的形象在一系列诉讼案中受人嘲笑。有些甚至受马里家族派系嘲笑,有一些还牵扯到哭泣者乐队(the Wailers)(披露:在这个案子里,我是哭泣者乐队的见证人。)鲍勃的遗产纷争十分有名,他的遗孀丽塔经律师建议伪造了鲍勃的签名,撤销自己财产继承人的资格。无论如何,代替鲍勃签名很明显是一个长久以来的夫妻习惯——鲍勃曾听天由命地叹息,经常告诉朋友,“丽塔签我的名字比我签得还要好。”从那时起,诉讼的结果对于诠释亲如兄弟的拉斯特法里派精神的乐队来说是一个难解之谜。两个乐队目前作为哭泣者乐队巡回演出,一个是主吉他手艾尔·安德顿(Al Anderton);另一个是偶像派低音提琴手阿斯顿(Aston)的“有家室的人”(Family Man)贝勒特(Barrett),他因诉讼而破产了。
同时,后鲍勃·马里帝国越来越庞大,从头戴式耳机延伸到衣服,休闲雷鬼观光游轮等等。
鲍勃曾在歌中预测,将来他的孩子们不会“坐在路边乞讨”,事实也如此。他教孩子们音乐,其中几个孩子如今已是成功的艺术家。鲍勃的11个孩子们没有经历他们父亲所遭受的社会约束和家庭抛弃,也没有经受使他变成一个激进分子和多愁善感的人的不幸。鲍勃在青少年早期退学,之后自学成才,而他的孩子们上精英学校。鲍勃的大女儿茜德拉(Cedella)是一位著名的时尚设计师,创造了牙买加奥利匹克队的形象,写儿童读物,现在正在制作音乐剧《马里》(Marley)。吉格(Ziggy)和罗汉·马里(Rohan Marley)追随他们农民父亲的步伐,发起生态产业链。年轻的孩子们在音乐上也有高产出。随着舞厅里像布珠·班顿(Buju Banton)和费步兹·卡特尔(Vybz Kartel)一样的歌手被囚禁,观众们也厌倦枪和懈怠,马里年轻的孩子们(主要是由达米恩(Damian)、史蒂芬(Stephen)、吉格(Ziggy)带头的)被视为牙买加雷鬼音乐的继承者,被称作“根源复兴”。在与嘻哈大师纳斯(Nas)合作时,比如《遥远亲戚》(Distant Relatives),特别是达米恩,他完成了父亲架起加勒比海与美国离散的犹太人的桥梁的夙愿。
现在鲍勃家族正在创立“马里自然”(Marley Natural)大麻品牌。“马里自然”毁誉参半,但却是适时的。忽然之间,大麻开始变成合法商品:马里的草植企业创造了工作机会。很多人希望这会改变牙买加的经济,甚至也许可以打破对旅游业的过分依赖。如果一切进行顺利的话,这个行业会产生鲍勃曾经向我提倡的滴流效应——以富人有责任用他们的财富做些事情为基础。鲍勃用嘲讽的语气批判那些人,“在银行里有3200万美元却没有一个工厂可以让其他人有份工作或是学习贸易的机会,你知道吧?他们只是想紧紧握住手里的钱——而钱只是像大海里的水一样。”
鲍勃关于如何生活的价值观和观念清楚明了,“你确定自己在做好事,”他告诉我,“虽然一直对别人好是困难的,但是你要尽力而为。上帝会回报你付出的一切,因为这是你获得回报的方式。也许你从别人那里获得物质上的报酬,但是你会从上帝那里得到精神回报。”
这就是鲍勃遗产的缺口——缺乏某些以他命名的中心教育或是公众文化的的努力,以展示其纯粹的利他主义。鲍勃各种成就已经在社会上引起注意——著名的有在加纳(Ghana)的丽塔·马里基金,支持一所乡村学校和妇女健康。但在众多热爱鲍勃·马里的人之中,很多人更期望看到在牙买加有组织的慈善活动,以此来证明鲍勃身体力行的利他主义;他因给排长龙的受难者现金而闻名于世,据估计,鲍勃非正式资助的牙买加人已有成千上万。除了自我牺牲,慈善是他成为传奇的一部分。
也许重点在于,无论马里的遗产用作何处,人们都会觉得这永远不够;你无法取悦每个人,那些被拒绝了的人可能会成为麻烦。而这关注点也许是真实的。无论财产如何,也许反对和平文化活动的暴力会被真正禁止。或者也许这是一个值得追逐的艰难的梦。当然,这样的动机会让全球的鲍勃拥护者欢呼雀跃,也将完成鲍勃1976年说给我听的愿望,“人们必须分享。”
我唯一一次看到他生气是他讲述在沟镇(Trench Town)的童年。“我那时居住在贫民区,每天得跳过篱笆,警察就试图抓住我,你明白吗?这不是一个星期的事——而是常年累月!多年来一直这样,直到现在我们自由了。要么你是个非常坏的人,他们枪杀你,要么你开始努力,让人们看到提高。这不一定要是物质上的提高,而是在思想上的自由。”
马里把烦恼的背景变成精神上生存的哲学,让音乐植根于人类本性并传达出去。因为正如他告诉我的一样,“我们成长艰难,但是这就是生活。有时候生活艰难,有时候简单。有时候每天都有问题接踵而来。青春就是随着 ‘生活是什么?我的未来在何方?’ 这样的问题长大的,因为每个人都在探索。” 鲍勃·马里在拉斯特法理派找到了答案。鲍勃70岁诞辰之日,在其出生地牙买加殖民地乡村,仍然有几百万人在他身上找到鼓舞、安慰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