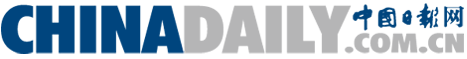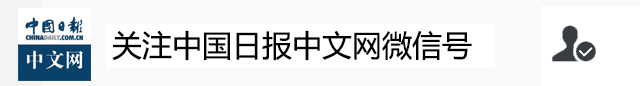《滚石》杂志一篇关于弗吉尼亚大学轮奸案文章引发的群愤正在渐渐消散,但是对此事的议论仍然延续着。苏珊·多米纳斯(Susan Dominus)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对许多女性而言、也许对相当数量的男性来说都同样熟悉的场景:异性中的一个好友正慷慨地斟酒,然后在一间漆黑屋里,在喃喃一连串“不要”之后,又有持续不断的央求声,最后是精疲力竭的屈服——因为这比鼓起勇气继续争论或者起身离开要容易得多。
当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与多米纳斯差不多的年龄,大学反强奸运动者的口号是“说不就是不”(no means no)。这话我自己亲口也说过许多次。它具有一条优秀社会法则应有特性:简单、易懂、容易达成共识。而今它仍是一条很好的法则,值得每一位男性和女性遵守。但不幸的是,对于许多女性而言,光有这条法规仍然不够。
我们以前把“约会强奸”无意识地套解为早年古老价值观的产物,但即使在早年,那种观念差不多也是古董了。在那个年代,按人们的想法女孩子要挺身抗争保护自己的处女之身。所以,(这种传言在男人中流传开来:)即使她们挺想做爱,也会大事张扬说不。因此,男孩子们会有办法找到一些女孩子应允的暗示——沙滩独步或者驾车进山——然后化解女孩各种公式般的推辞。有时,这或许真的是两人的共同期盼;但常常并非如此:那些男人便是强奸犯。
我不知道以前年代的描述是否准确,因为我没在那年代生活过,但是我听到了够多的故事,让我觉得至少大致说出了事情真实的一面。抛开准确性不说,我们相信这些价值观念也是我们以前也在正在抗争的。因此,我们“说不就是不”,女孩应允与否应以她明确接受为前提,无关她那时穿什么、或者你觉得她同意回到你的卧室。
“说不就是不”这句口号是否有足够力量防止舞会时的“约会强奸”,我们姑且不论,但它肯定不足以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难道题。我们这一代比我们母亲那一代喝地更多,经常是要不没法说不,要不连话都说不了。也没有什么寝室制度不让谁走进别人门,或者强迫我们在夜间早点归巢。我们也不能用“好女孩才不会”作自己拒绝的理由——每次要拒绝的某一个男子,不是因为有什么外力阻止我和他做爱,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与他做爱。就是因为聊天不爽,即使我们可能很现代,但大多数女性仍然不喜欢那种不舒服的交谈,尤其是喝了几杯想睡的时候。
我不是呼吁恢复男女生分楼或宵禁制度,也不提倡“乖女孩才不那样”的处事态度。我只想强调,正是这些东西帮助了我们母亲那代人容易说出“不”字,不用解释、不会冒犯谁,也不会被看成是对眼前那人的全盘否定。我们现在称颂的口号,是一句为已不复存在的世界设计的口号。在当今世界,说出那样的话需要斩钉截铁的意志力和对自主能力的自信,而这正是许多19岁女孩难以鼓足勇气做到的。它还需要我们做出平时不愿做的事情,比如大声说“不”,而且如果他强求就起身离开。换而言之,我们落入了一种无助的境地,尽管与我们母亲那代人经历的方式不同。
多米纳斯建议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语言,消除这些有害无益的现象:
我渴望能在那一刻有更多用得上的词汇,此后我努力想要找到一种能够表达那刻经历的言语。那晚我想要的是一种语言上的“用具”,一种既没有“不”字落俗的熟悉感,又没有“滚开:要不我喊了”的强烈感。
当然,“不”和“放手”还是该用,也该得到尊重。但有几位女士告诉我,当对应允与否仍感觉摇摆不定的时候,那一刻来临时她们整个人就变得呆若木鸡,无话可说了,结果她们什么也没说出口。那些话自然会得罪人,说出来需要一定程度的意志力,但这种意志力正是那个身处压力内心迷茫,或是觉得后怕又改主意的女性无法拥有的。
……一种管用的短语或许是“红区”,比如在“喂,我们到红区了”,或者“这有点太过红区了”。既形象又就事论事,不会把谁明确划分为侵犯者和受害者,只会直截了当地传达一种信息:危险近在咫尺——情感上,也许法律上的。这个词语做为一种语言替代,兼具那一刻均不可能的两种选项的功能:接着抗拒或继续强求。“我们到红区了”,说这话的人不是央求者(“求你了别”),也不是指责者("我让你住手!”)。不过,许多年轻女性哪个角色都不觉轻松,我以前也这样。
我明白多米纳斯的意思,但是我不觉得她的办法有用。从大学注册入校到现在的25年里,我们一直在物色另外一个说法来取代“不”字那种旗帜鲜明的简单。不幸的是,根本就没有能替代的。如果你打算“教男人不要强奸”——一种在《滚石》发表的文章数天后就出没在网络上的说法——那么你需要给他们一个既明白晓畅,又切实可行的法规,哪怕也有其它的。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说不就是不”并非十全十美,但仍然很管用。它是一种经验加常识,连一个忙着吮吸一根从三层楼高垂下来的啤酒管的家伙也能记得住,做的到。当然,这个法则无疑需要一些注解,可以加上其它同样清晰的规则,如“如果她醉得踉踉跄跄或开始呕吐了,就全当她说过不字,因为从法律角度上她失去了应允的能力”。在现代性爱习俗的世界——一个经常令人迷茫、负担风险世界里,你得认真听女伴在说什么,别想成她是在给你传递什么口不应心的绝密信息:这种基本认知便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需要的法则。
再与“我们到红区了”比较,那是表达什么意思?于我而言,似乎是一个男的可以有两种理解:当成“不”;或者程度没到“不”,而后者似乎是说还有戏、他应该考虑着过个15分钟接着央求。如果这句话是指“还没有到‘不’,但是处在‘不’与‘是‘之间”,那我们啥也没解决,除了让人更犯迷糊。
但是,我倒不认为那是多米纳斯的目的,我觉得她其实是找一种表达拒绝的方式,既清晰明了、又无需说出“不”字。作为与她同时代的女性,我们都有同感:经常,为了避免给男人一种哪怕很委婉的拒绝,要使出可用荒谬来形容的力气,诸如回绝我们不想要的花费或殷勤。我当然希望有靠谱的方法,不用说出那些话又可以传达信息。
但正如数以百万计室友证明的,别无它词可以替换一个清晰明了的“不”。我这代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创建新词取代刺耳的旧词,想通过此法让事情顺耳些。这种“委婉语跑步机”——正如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昵称所称,练的结果不是每人走向新的更高的平台,摆脱旧日的烦恼。事实上,新词具有旧词所有的寓意,然后,人们又开始寻找另外一种委婉语。
“开水房”(Water closet)变成了“厕所”(toilet)——最早指大众洗身的一个词,就像用在“清洁用具”(toilet kit)中,然后又变成了“卫生间”(bathroom)、“洗手间”(rest room)、“盥洗室”(lavatory)。“垃圾回收”变成了“卫生清洁”,又变成“环境服务”。
这种委婉语跑步机说明,是概念,而非词语本身在起主导作用,也就是说挑个概念给它一个新的名称,再让名称具有概念的特色。但是,概念本身并不因为名称具有新的含义。(当这个国家少数民族的称谓不再变来变去之时,便是我们得知实现了平等互敬之日。)
我们女性挣扎的并不是“不”这个字,而恰恰是人们,也包括我们自己对那种断然拒绝的认识。这是一定要改变的,而不是改变哪个描述的字眼。这样一个负担也许不应该就这样落在女性身上,尤其是当我们被社会调教要依从、要“乖”(尤其对男人)。不幸的是,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帮我们承担这个负担:一种决定我们愿意和谁做爱,然后清楚有力地表达出来的负担。
女权主义者也不用那么热切地帮助女性摆脱做决定的负担、或是让她们避免用最有力的语言大声表达观点。“不”和“我不要”是女性要掌握的有力工具。几个世纪以来,社会替我们决定女性需要什么、惩罚那些有所不从的女性,并通过这种方式庇护顺从的中产阶层女性不使用这些词。现在那些规矩终于不复存在了,但是女权主义者却又在鼓吹让我们把作决定的负担转交给…..男人们;这样一来,他们就得东猜西揣我们给的是否属“确定”应允,一旦猜错便会被惩。
在我看来,这些“确定”应允法则不论作为社会还是法律标准来看都完全无用。更恶劣的是,它们又交回了我们奋斗很久才得到的权利:为自己做主的权利,以及因自己的决定或获得奖赏或承受后果的权利。“说不就是不”是一个足够好的法则,虽然不足以击败每一个利用药物或强力得到女性的并非免费东西的惯犯,但足可打败一种“强奸文化”,一种指女性不懂她们真正需要什么,或者不值得让人尊重她们愿望的文化。
但是,即使一个好的法规也需要能使之成为现实的明智女性:以自己的决定为自豪,对自己的自主权利充满自信,有足够的勇气承受令他人失望后产生的尴尬——那些极力想要,我们却不想给他们的男人。女性需了解“不”字,不仅保护自己避开卧室里的蛮横之徒,也会让她们在外部世界更强大有力。我们应该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拥戴“不”字,并让男人知道我们会更多的说“不”字。我们应该坚持对任何事情都有发言权,而且我们的意见和男人们的一样算数。
因此,我们需要告诉男人们“说不就是不”,对这个简单法则的任何违背都伴随严酷的惩罚。但是,我们女性也需要告诉他们“我的意思就是不”,不是告诉他们“我们到红区了”,或者“我不能,我明早有课”。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告诉女性同胞:说“不”是她们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权利,被给予了这些礼物的人有责任去使用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