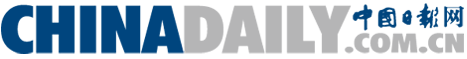编者按:1937年到1945年,曾有很多外国人在中国生活或服役。有关他们的经历,我们进行了系列特别报道。此篇是系列报道的第七篇。
悉尼·格林伯格是美军164照相连的一位老兵。这些是他二战时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美军老兵悉尼·格林伯格(Sydney Greenberg)的儿子菲利普回忆说,父亲睡觉时,“走廊里点着一盏灯,床头放着一只手电筒,这一习惯从未改变”。
2012年1月,这位老兵去世了。那一年是他从中缅印战区回国后的第67个年头。中缅印战区是二战战况最激烈的战区之一,但相关报道却是最少的,那里也是他一手拿枪、一手扛着照相机走遍的乡野土地。
“我父亲是美军164照相连的一员,被派遣到中缅印战区拍摄照片。”菲利普·格林伯格在回复《中国日报》的邮件里这么说。“有一天晚上在中国,士兵都熟睡了,这时候日军潜入营帐里——我父亲和队长睡在靠近营帐中心的吊床上,周围都是中国士兵。当我父亲醒来时,他发现周围大多数士兵惨遭割喉。看来日军先从睡在营帐边缘的人下手,慢慢深入中心,杀死了离他们最近的士兵。从那一刻起,直到他去世,我父亲始终没能摆脱对黑暗的恐惧。”
悉尼·格林伯格在中国西南边陲地带呆了两年,期间拍下数千张图片。这些照片并没有萦绕着黑暗的阴影,相反,他的影集略带暖意,描绘诗情画意的乡村风景,只是用一名士兵作为背景图将战争一带而过。在其中一张照片中,一位摄影师用电影摄影机给中国孩子们拍摄,巧妙捕捉了男孩们的想象力。
“我父亲拍摄的大部分照片表现出在战火纷飞的地带,中国人如何努力让日子略微稳定下来,怎样应对眼前的日常生活。照片记录了他身边的人——身陷战争泥潭,与他休戚与共。”菲利普说。
悉尼·格林伯格和五个中国男孩在一起。1944年摄于云南。(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士兵兼艺术家”
1943年末,悉尼·格林伯格到达云南省会昆明。“一到这里就遭到了另一场袭击,”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这位时年23岁的摄影师和他的同事刚在海上度过一个多月。当船抵达印度时,这支250人组成的连队的军官们、各级人员、摄影师与暗室技术员都被分成两个人数相当的小组,其中一支留在印度,另一支则前往中国。格林伯格就在后一支队伍中。
纪录片导演﹑业余历史学家牛兹将164照相连的摄影师称为“士兵兼艺术家”。他说,这些照片见证了中缅印战区被忽略的战争历史。
“二战期间,美军在所有海外战场都派遣摄影连队。从这个角度来说,164照相连并不特殊。然而,要知道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边陲,照相机绝对是稀罕物品。黑白照片与电影片段并不仅仅是历史脚注,更是历史本身。”
美军164照相连的大量照片都被收藏在位于华盛顿的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2010年,牛兹和他的朋友们用了两个月时间在那里查找资料、影印文件、记录史实。只要与中国以及二战中缅印战区有关的内容,他们绝不遗漏。
晏欢陪同牛兹一同前往华盛顿,他的外祖父潘裕昆曾在中缅印战场任中国国民革命军将军。“总共大概有2.3万张图片。几乎全部印有‘Signal Corps’或‘US Army Photo’的图片都是164照相连队的摄影师拍摄的。”晏欢说。
在“战地摄影师”一词在现代战争流行开来以前,那些战地摄影师们就已经与战争“不可分割”了。“我父亲过去常说:‘我们和中国人生活环境相同。我们吃的、喝的、睡觉、穿衣都像是中国人。他们不洗澡不洗衣的话,我们也不洗。这样最终我们闻起来味道相同。”菲利普说。
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美国士兵的穿着与中国步兵一样,脚蹬一双绳编鞋——这么穿是有原因的。“中国士兵劝他们不要总穿着美军统一发放的制服,因为日军热衷于寻找级别最高的美军人员,并向他们开枪射击。”菲利普·格林伯格说,“我父亲的队长就被日本狙击手打死了,他带了一顶美国陆军头盔。”
虽然美国士兵通常都能很好地适应新环境,但还是有些饮食习惯让他们难以接受——每顿都吃米饭配蛇肉或啮齿动物肉已令悉尼·格林伯格难以下咽了,喝未经消毒的地沟水则雪上加霜,他患上疟疾和痢疾,体重因此减半。
尽管困难重重,格林伯格仍对中国人敞开心扉。在船上时他已学过“‘中国礼仪”(举止得体),这个士兵摄影家还发现了一个与中国人交好的“秘密武器”——烟。
“我的母亲在国内一家供应机构上班,她经常寄给父亲许多香烟。”菲利普·格林伯格说。父亲把这些烟分发给当地居民,于是人们对他更加亲密。因此,他照片中的人物看起来毫无防备,悠然自得,比如一位幸福的母亲怀抱咧嘴微笑的女婴。
格林伯格最有名的一张照片描绘了一名持枪的中国士兵挺身站在坦克上的背影。在雨季,士兵抬头仰望天空,一架美国飞机冲破云霄,给盟军空投食品。尽管天色阴郁沉闷,云朵低飘,呈现出世界末日般的气氛,但是士兵高挺的身姿就像一盏希望的灯塔,象征着顽强不屈的抗争力量。
虽然经常有中国士兵保护摄影师,出于对重型摄影器材和人身安全的考虑,摄影小组通常不会在战场前线拍摄。不过,他们还会面临其他没那么致命的敌人。
“赫奇的35毫米柯达相机今天遭到白蚁侵袭。”悉尼·格林伯格在日记中写道。赫奇是他的同事亚瑟·赫奇,也是一位摄影师。“看起来好像是他把相机挂在树上,然后一只怀孕的白蚁爬进镜头上端开口处。今天下午拍照时,他突然发现镜身里爬满了无数只白蚁;所以下午的后半段时间,我们别的什么都没干,就用烟把白蚁熏出来。”
他又写道:“晚上,我把相机放在防雨罩里,然后又放进野战背包中。第二天早上打开包一看,机身周围甚至是镜头盒里都是绿色霉菌。”
这些照片被送到初始加工实验室,事实上就是土质建筑,那里有从药店借来的有些老化的磅秤,用来称化学用品,以供把照片连夜冲印出来。
悉尼·格林伯格在日记中描述道,当这些士兵不拍照时,就“坐在防空洞的战壕里,看手榴弹爆炸,记下他们的所见所感”。“就像电影一般,火焰点亮天空……红色、蓝色、绿色、还有白色的,少校告诉我们,头三个日军据点已经是我们的了。”
1945年9月9日,日本在南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的南京英文名还是“Nanking”。
二战结束了,悉尼·格林伯格负责协助拍摄这一值得欢庆的日子。“在南京,我父亲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直接飞往上海,从那搭船回美国;二是回到昆明,也就是他抵达中国的城市,然后去印度,在那里乘船回国。”菲利普说,父亲选择了后者,以回顾他当初踏上中国土地的经历。
一位士兵摄影师给当地孩子们拍摄连续镜头。(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战后“朋友”
战后,悉尼·格林伯格继续拍照。他还在家乡担任太平绅士,一当就是40多年。一家当地报纸在讣告中这么形容他:这个职位让他为无数对情侣主持婚礼,他讲究排场,注重氛围,诙谐幽默的风格无与伦比。
他还定期开讲座,讲述他在中国度过的日子。他虽然喜欢中国,但他并不想回去。菲利普说,父亲不愿让回忆的湖水泛起涟漪。
2011年,年迈的格林伯格非常高兴地得知,包括牛兹与晏欢在内的来自中国的历史爱好者们,正准备在重庆安排一场会展,陈列美军164照相连的作品。时年92岁高龄的格林伯格受邀出席展会,但由于他车祸后健康有待恢复,因此无法远行。于是,他录下一段视频,在展览开幕式上播放:“一个崭新迷人的世界展现在我眼前。你们待我如朋友。”他用汉语说出了“朋友”二字。
相机和卡宾枪是相机连的两个重要武器。(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1944年左右,格林伯格流利的汉语使他得以与蒋介石见面。“当我父亲问道:‘我可以给您拍一张照片吗?’’蒋介石便从一大群记者中转过身来,对他微笑。镜头便定格在蒋介石身上。”
年轻的格林伯格当时被分配实时拍摄蒋介石的飞行视察之旅。在飞机上,格林伯格还教会他如何使用35毫米莱卡相机。
今年早些时候,晏欢在浏览自己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拷贝的照片时,一张从未见过的照片让无语凝噎——照片上是格林伯格本人。晏欢说:“如果2010年你和我同在国家档案馆,那么你就知道我们是多么频繁地见到背面上印有‘S.L.格林伯格’名字的照片。但这张是格林伯格本人的照片,而不是他拍的照片。所以它弥足珍贵。”图片中,格林伯格和五个中国男孩共同坐在一辆军用吉普车里。晏欢与这位老兵一直通过邮件联系,当他去世时,还向其家属发来慰问信。
“恐惧和惊异;用几年时间拍摄照片,却是一生的冒险之旅——这就是我父亲心中中国之行的意义。”菲利普说。在其父的激励下,他后来也成为一名新闻摄影记者,为美国主流报纸与杂志完成了2300多项拍摄任务。“我追随父亲的步伐,继承他的事业。”
回顾父亲二战时在中国的经历,菲利普表示:“他们(中国人)友善待人,花时间陪伴他。他则每天给他们拍照片,以示尊敬。”